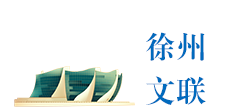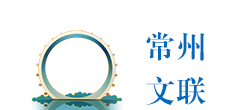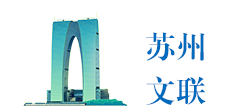微观显影、空间隐喻与图像正义
——评电影《南京照相馆》
文 |郭培振
由申奥导演的电影《南京照相馆》在今年暑期档票房领先、口碑载誉。观察近年来暑期档头部影片可以发现,其票房的制胜关键无不在于精准把握“社会情绪”:《孤注一掷》洞察诈骗之痛,《抓娃娃》聚焦“鸡娃”教育之困。而《南京照相馆》在此意义上更进一步,成功唤起观众深沉的“民族情绪”,以影像铭刻民族抗战史。
影片取材于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真实罪证影像,用照片揭露日军侵华的亲善假象与残暴事实,照见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战信念与“寸土不让”的民族信仰。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南京照相馆》与同档期的《东极岛》、即将定档的《731》等作品,共同以影像定格历史、唤起记忆、致敬英雄,显影崇高的民族精神与正义话语。

类型突围:抗战叙事的三重定位
《南京照相馆》在中国战争题材电影的叙事创新与类型定位在于:
其一,显影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电影的中国话语。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国际上基于西方立场的“二战”叙事却往往缺席中国抗战力量。在此背景下,中国抗日战争题材电影理应弥补此不足,讲述关于中国人民的抗战故事,记录并传播反法西斯题材电影的中国话语。
其二,持续推动中国战争题材电影的微观叙事转向。一方面,叙事视角从宏大战争场景转向平民生活现场。自《铁道游击队》《血战台儿庄》至《八佰》《长津湖》,战争题材电影多聚焦重要战役,形成以战斗场景为核心的叙事模式;而《南京照相馆》则以冲洗照片为主线,透过七位普通市民的视角,铺展战争全景,彰显“微光撕裂黑暗”的真实情感力量。另一方面,人物塑造从革命战斗英雄转向平民英雄群像。《英雄儿女》中王成喊出“为了胜利,向我开炮”,体现中国人民投身革命事业“向死而生”的崇高信念,由此,无畏牺牲、勇敢坚毅的战斗英雄成为战争电影的主要形象;《南京照相馆》则聚焦邮递员、照相馆老板等南京市民,细腻刻画其从挣扎求生到精神觉醒的伦理抉择与人性光辉,由此凸显战争洪流中普通民众所凝聚的坚定抗战信念与民族信仰。
其三,聚焦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事件真相。申奥作为新一代导演,其战争影像话语不同于前人导演拍摄的同题材电影。如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与陆川的《南京!南京!》,二者在中美、中日人物关系的塑造上受到争议,在钻研人性与历史哲思的维度上难以避免“宏大”视角。相较之下,《南京照相馆》抛去一切“杂念”,以近乎执着的姿态回归事件本体——为历史作证,为真相发声,聚焦于揭示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
同时,照片罪证的故事曾在1987年《屠城血证》中有所呈现,但该片以“南京安全区”的中国医生为视点,侧重争夺照片过程中的势力斗争,对“真相显影”所激发的人性微光着墨有限。《南京照相馆》的突破还在于其最终定格了日军战犯伏法的正义瞬间,为观众积郁的民族情感提供了宣泄出口。
综上,影片以微观史学为纲,以平民群像为本,以历史真相为准则,以人民抗战信念为精神主线,实现了中国战争题材电影的创新突破。

空间隐喻:照相馆的三重坐标
影片的核心叙事空间是南京城一隅的照相馆。这一空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与战斗空间、国际声援空间的联动,承载起多重深刻隐喻:
其一,照相馆是战时百姓求生的生活空间。影片通过能够外出的苏柳昌、王广海等人视角,带领观众见证日军对百姓的屠杀、对家园的破坏。由此,照相馆的生存价值显得愈加珍贵,成为苏柳昌等人求生的依靠。但照相馆成为所谓的“临时安全区”是由于日军洗印照片的需求,这一矛盾赋予了照相馆本身足够的戏剧隐喻与话语博弈。
其二,照相馆是连接国土符号与民族记忆的精神空间。随着照相馆老板金承宗拉起一张张背景幕布——万里长城、故宫、城隍庙、黄鹤楼……苏柳昌等人逐一辨认出这些铭刻着民族记忆与家国信仰的建筑符号。而彼时,这些地方正遭受日军的野蛮践踏与侵占。影片在此唤起人物与观众心中“大好河山,寸土不让”的坚定民族认同。
其三,照相馆暗房是真相显影与反法西斯共同体力量凝聚的象征空间。确证日军罪行的底片在暗房中逐渐显影、定影、停影。特写镜头中一张张触目惊心的照片在暗红色光影中“跃出”,仿佛弥漫着血腥气息。林毓秀等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将这批“不许可”的照片缝入衣内,誓将真相公诸于世。最终,当罪证照片登上各国报纸头条,汇聚成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声援中国的声音,彻底戳穿了日军精心编织的“亲善”谎言。
在平凡的照相馆中,平凡百姓以“向死而生”的信念向世界显影真相,显影不平凡的人民信念。

图像正义:照片的三重证词
定格历史,照亮正义。W.J.T.米切尔认为图像是充满话语隐喻的叙事符号。照片不仅是可视的、历史在场的图像,还是“不可见”的媒介,具有叙事隐喻与权力话语的不可见性。《南京照相馆》中的南京百姓生活照片、日军集体合影、“亲善照”与日军在南京的罪证照,成为揭露日军罪行的多维证词:
其一,“照片何为”——日军侵入南京城的合影指向侵略事实的历史在场。经由日军摄影师拍摄的日军进城仪式、日方士兵在南京城建筑的合影具有图像的言说能力,其背后透露出日方的侵略欲望:对中国国土的武力侵犯、对中国人民的精神侵犯与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侵犯。当苏柳昌将照相馆墙壁上悬挂的百姓照片换成日军照片,又亲手将后者一一打落时,他作为“照片的显影者”代替图像言说“我们不是朋友”的话语诉求。
其二,“照片何求”——南京城百姓的生活照与日军伪造的“亲善照”分别显示出图像的抵抗与暴力隐喻。南京城百姓的夫妻照、全家福、学生照等击溃了伊藤秀夫的心理防线,彼时金承宗的画外音暴露出图像生产过程的叙事隐喻,即中国人民安居乐业、向往美好生活的民族话语;而日军强迫百姓拍摄的“亲善照”则进一步暴露出图像的暴力生产机制,批判日军企图控制国际舆论、稳固战争局势的政治话语。当图像生产现场成为日军对孩童的虐杀现场,战争宣传已然陷入了有关媒介真相的话语困境。
其三,“照片何能”——确证日军侵略罪行的“京字第一号证据”书写了图像的正义潜能。影片中将相机拍摄动作(装胶卷、按快门等)与枪杀动作(装弹、扣动扳机等)并置剪辑的段落有两处:一处是伊藤秀夫拍摄日军枪杀战俘的画面,后续由此拍摄的一系列“不许可”照片成为审判日军罪行的铁证;另一处是林毓秀拍摄日军战犯被枪决的画面,这一定格性的瞬间具有确证历史真相、彰显图像正义的叙事隐喻。两处首尾相衔的剪辑呼应既是图像正义的书写,也将观众的情绪落在了实处。

影片通过相机“定格”的见证性、胶片“显影”的真实性、历史“索引”的正义性,揭露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罪证;也通过人物的伦理抉择与精神觉醒,深刻唤起观众自觉、自发的家国情怀与民族认同。“照片能褪色,但历史不会——它只是等有人翻开。”这是《南京照相馆》对待历史真相的态度,也是中国人民的态度。
作者简介
郭培振,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生。
来源:谈球吧文艺评论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