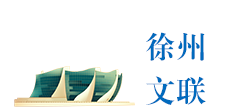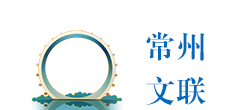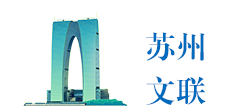《南京照相馆》的三重“显影”
文 | 张红军
《南京照相馆》以1937年南京大屠杀为历史背景,从“小切口”讲述了几位避难于“吉祥照相馆”中的平民百姓守护历史真相、冒死传递日军罪证底片的故事。“显影”作为电影中的一个核心隐喻,在物理、精神、文化等维度显露出多重深意:在物理的暗房里,它让模糊的罪证逐渐清晰;在精神的废墟上,它显影出绝境中人性的微光与不屈的灵魂;在文化的长河里,它更将那段伤痛的记忆显影成民族血脉中永不褪色的烙印。

一、物理显影:底片承载的残酷历史真相
电影的第一重“显影”是侵华日军胶片上的物理显影。“显影”是胶片摄影中至关重要的一步,是指在胶片冲洗过程中,通过化学处理(显影液)将胶片上的不可见潜影转化为可见的、稳定影像的过程。影片中,暗房内泛起的红光成为全片强烈的视觉符号,显影液让潜藏在底片上的日军残暴行径浮出水面,将不可见的瞬间定格为可见的铁证,让残酷的历史真相得以显现。当苏柳昌(刘昊然饰)搅动显影盘,底片逐渐浮现出来的影像并非是日常市井烟火,而是日军在南京城里烧杀抢掠的一幕幕暴行。这是一段血色记忆,留存于真实存在的“京字第一号证据”相册中。在暗房空间内,在显影液、红光与鲜血的色调重叠下,这些照片再次成为唤醒民族伤痛的视觉象征。
影片中的一个情节充满讽刺意味,大量记录暴行的照片因有损日军“形象”被盖上“不许可”印章,取而代之的是强迫百姓摆拍的“亲善照”。自摄影术诞生以来,影像便被认为具备记录真实、保存记忆、“见证”历史的属性。而同时,影像也受福柯所言的权力话语所宰控,成为政治和宣传的工具。《南京照相馆》精准地戳破了照片的这种“两面性”。日军用“不许可”强行抹掉罪行,又妄图用刺刀“导演”出一幅虚假的和平景象,照片在此成了他们粉饰太平、掩盖血腥、开展舆论战的工具。而在方寸的吉祥照相馆中,避难的金老板(王骁饰)一家、假冒的照片冲洗工苏柳昌、龙套女演员林毓秀(高叶饰)等这些本与宏阔历史无涉的小人物,却以他们各自的平民故事,完成了一场艰难又悲壮的接力,让刻意遮蔽的历史真相得以被守护并最终“显影”于世人面前。

二、精神显影:平民觉醒与复杂人性光谱
照相馆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片中几位主要人物从“保命求生”到“保存罪证”的心理变化,展现出残酷战争中的复杂人性光谱,也是对国家危亡时刻民族精神的显影。这些也向观众传达着:底片是无声的证词,而普通人在绝境中的选择,才是民族精神最坚实的支撑。
原本是邮差的苏柳昌,为了活命阴差阳错做了照相馆冲洗工并与日军虚与委蛇,一次次被迫为日军冲洗屠杀照片后,被灼伤的良知逐渐由麻木转向觉醒,终于在临终前对日军摄影师伊藤秀夫说出那句:“我们不是朋友”,完成对自身民族身份的确认。带着一家人藏身地窖的照相馆老板老金,最初只为能在乱世中苟活。但也正是这样一位有点贪生怕死的小人物,在看到被冲洗出来的日军暴行照片时清醒地说:“这些照片洗出来,我们就都成汉奸了”。很快,他就开始思考怎样把底片缝进大家的衣服里带出去而不当亡国奴,并且在女演员林毓秀被日军侵犯时第一时间从地窖冲出来救人,最后为保护林毓秀和小孩独自走向日军的枪口。当南京城破、众人仓皇逃命之际,女演员林毓秀却反常地端坐梳妆台前,画着日本国旗、练习日语。她幻想依靠情人王广海(王传君饰)的庇护,为自己换来一张通行证。然而,随着她移至吉祥照相馆,亲身经历了日军的凌辱,并目睹了在拍摄所谓“亲善照”时日军将婴儿活活摔死的暴行之后,她开始意识到妥协与退让根本无法换取生存,她内心沉睡的民族血性被激发,掷地有声地说出“我从小学的戏,是穆桂英和梁红玉”“万一日本人真的输了呢”,这标志着她从怯懦、投机到觉醒的蜕变。电影正是在对这些普通人的“人物弧光”塑造中,完成了对中华民族不屈灵魂的精神显影。

三、文化显影:主体性与自我救赎的强调
《南京照相馆》的另一重深刻意义,在于它实现了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文化显影。电影取材自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真实罪证影像,在其上映前,相关题材的影视作品已不鲜见。然而,这部电影之所以展现出强烈的当下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它以一种自我救赎和不卑不亢的自信姿态来反思历史、直面创伤,从而重新锻造和凝聚民族精神,这与当下社会文化和观众情感产生了深度共鸣。值得注意的是,电影摒弃了以往一些作品选择的“他者”视角,即将自身文化与历史悬置、中空化,意图借由他者之眼来讲述自身故事,从而制造出一种“被救赎”的幻想,导致历史记忆模糊与身份主体认同的困惑。相反,《南京照相馆》是以一种主体性视角传递“大好河山,寸土不让”的信念。影片中反复出现的“城门城门几丈高”南京童谣,穿插于电影中的鸡鸣寺、莫愁湖、中华门、紫金山、挹江门等南京地标,以及片尾彩蛋中昔日被日军侵略下的断壁残垣与今日繁华城市景象的重叠对比,这些不仅能唤醒观众的熟悉感,更有效激发了国人的集体认同和爱国情感。
影片并未将日本人或反派角色塑造成一种弱化、片面化的形象,在日军摄影师伊藤秀夫、翻译王广海身上,观众甚至可以感受到人物的复杂性。同时,影片也有意规避了对悲惨场景的奇观化呈现,比如在表现妇女、儿童被日军欺辱的暴力场面时,采用了克制、留白的手法。恰恰是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在重塑战争认知和深化历史反思方面,产生了更为深刻的穿透力和震慑人心的效果。

真实是历史的锚点,遗忘终将导致悲剧重演。《南京照相馆》既是一份关于历史暴行的影像证词,更是从物理底片到民族精神,再到文化认同的三重“显影”。它超越了单纯的历史复刻,通过聚焦照相馆方寸之间普通人的抉择与蜕变,向观众传递着:个体也能成为守护民族尊严、抵抗历史遗忘的坚韧脊梁。片尾的“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不仅是一种信念和警示,更需要每一个“吾辈”躬身践行。
作者简介
张红军,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教授,江苏紫金传媒智库理事长,谈球吧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来源:谈球吧文艺评论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