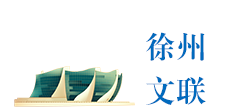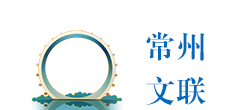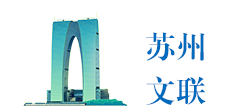《南京照相馆》作为一部聚焦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的电影作品,其叙事视角和表达方式与国内以往同类题材作品相比发生了显著变化——以普通人视角重新讲述那段历史、选择以克制的态度呈现暴行等,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以85后为主体的新一代电影人创作理念的进步,更深层次地折射出当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崛起。这种创作转向,本质上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主体意识觉醒在电影艺术领域的具象呈现,当代国人的民族自信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精神重构。
一、普通人视角下的大屠杀
《南京照相馆》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它的人民史观叙事立场,它是国内首部从普通人视角或者说遇难者视角去讲述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同时,它清醒的看到了普通人在抗日战争胜利中的重要作用。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以3500多万军民伤亡的巨大代价换来的,但此前还未有电影如此浓墨重彩的呈现人民在抗战胜利中价值和作用。
中国电影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再现,长期存在着某种叙事惯性——或通过《屠城血证》中展大夫这样的知识分子视角,或借助《金陵十三钗》里约翰这类“救世主”形象,或依托《南京!南京!》中陆剑雄等军人角色,而《南京照相馆》则将镜头对准了最普通的中国人——邮差阿昌、演员林毓秀、照相馆老板金承宗一家。观众仿佛经历了一场大逃杀,跟随他们的视角共同经历那血腥的六周里普通人到底遭遇了什么,带入感极强。试图出城的,如苏柳昌的同事们,尚未触及城门便湮灭在炮火中;滞留城内的,如苏柳昌本人,只能在断壁残垣间惶惶如丧家之犬四处逃窜;幻想战争结束后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的,如金老板一家,只能躲在地窖里时刻承受着饥饿和恐惧的双重煎熬;而选择投敌当汉奸的,如王广海之流,机关算尽、卑躬屈膝最终不过是一场空。电影全景式还原了大屠杀期间南京城的众生相,然而不论怎么选,都是必死的结局。在这样的叙事视角之下,老百姓不再是面目模糊的一串“数字”、被凝视的他者形象,而是面目清晰、有血有肉的历史主人翁。

人民史观强调历史不仅仅是英雄、帝王将相或宏大事件的记录,而是由无数普通人的选择、抗争与生存共同塑造的。《南京照相馆》正是人民史观在文艺作品中的完美实践。电影中那些记录暴行的照片,既是历史的铁证,更成为了普通民众抗争的武器。为了让记录日军暴行的照片成功送出,《屠城血证》中的照相馆老板、进步知识分子和歌女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也绝对少不了外国友人的帮助和日本特权阶级的庇护。而《南京照相馆》则是一场纯粹由普通人完成的生死传递:阿昌等五人将照片缝进衣服里,最终只有林毓秀一人抵达安全区——这个残酷的生存概率,恰恰印证了人民抗战的悲壮与惨烈。导演申奥在访谈中说道:“14年抗战,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一场人民战争的胜利,是千千万万中国人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才最终赶走了侵略者”。电影正是通过展现以阿昌为代表的普通中国人从求生自保到舍身救国的觉醒之路,诠释小人物在抗战胜利中也有他们的价值,证明“人民也能创造和改写历史”。
二、暴力场景的克制:从“悲愤控诉”到“警醒铭记”
导演申奥在路演中表示:“我们拍这部电影的目的,不是为了展示血腥暴力,而是要表现国人在暴行中的勇气与希望。”与1987年的《屠城血证》和2011年的《金陵十三钗》不同,对待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2025年的《南京照相馆》不再声嘶力竭的控诉,而是学会了克制的表达,视觉刺激强烈的暴力奇观尤其是对女性不友好的镜头少了很多。
当日军车辆碾压平民尸体的场景出现时,导演选择将镜头拉远拉高,俯拍的远景镜头避免了细节性展现暴力场景,观众只能听到车轮碾压血肉的声效。日本士兵摔死婴儿的那场戏,镜头尽量回避婴儿的正脸,日本士兵残暴的行为被简化成一个简单的抛掷,随着一声沉闷的“咚”响,一直哭闹不休的啼哭声戛然而止,画面给到的是在场者情绪崩溃的面部特写。

此外,女性受侵犯的场景也少了很多,而且也不再直观呈现转而用细节暗示,如疯掉的凤华机械的用日语重复念叨“欢迎光临”,林毓秀给日本人唱戏回来后头发凌乱、眼神空洞、衣衫不整,金老板的妻女出逃前果断的剪掉了长发等等。对于暴行的克制表达,彰显了新一代电影创作者的历史自信——不再需要通过视觉暴力来表现历史真实,而是以更富尊严的方式讲述民族伤痛。
回望中国抗战题材电影的历史,苦难叙事的底层逻辑曾长期主导此类题材的电影创作。在综合国力远弱于日本、民族创伤尚未痊愈的历史语境下,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电影人在回望那段惨痛的历史时,集体意识是悲愤、无奈的,往往会采用纪录片式的方式真实的再现暴力细节:断裂的肢体特写、赤裸的性暴力呈现,镜头因过于残忍血腥甚至会引发观众的生理不适。而《南京照相馆》的不同在于,它在克制中完成了对历史的叩问。这种叙事方式转型的深层动因,源自当代中国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以申奥为代表的新生代导演成长于中国经济快速腾飞的黄金时代,身处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已经拥有有足够的底气更加冷静克制地面对伤痛。正如阿昌在临死前斩钉截铁的对伊藤所说的那样,“我们不是朋友”。即使现在中日在官方层面是友好邻邦,但面对日本我们仍要时刻警醒,唯有自强不息,方能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三、突破性的汉奸形象:直面历史中的投降主义
汉奸翻译官王广海这个人物是真实且复杂的,算是电影中塑造的比较成功的角色之一。
一方面,他虽是汉奸,但良心并未完全泯灭。他知道阿昌是邮差,但选择了帮他隐瞒,救了他的命;他目睹婴儿被摔死,会不忍、会痛苦,险些情绪失控;他一次次选择助纣为虐,然而当林毓华的求救声刺穿他的心理防线时,他一直被压抑的血性和良知还是觉醒了,短暂的反抗后等待他的是死亡。

另一方面,相较于以往抗日题材电影对于汉奸的塑造都是比较单一的纯恶人形象,王广海这个角色打破了汉奸脸谱化的创作惯性,开始深究他们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动机。要理解为什么王广海和林毓秀最初选择亲日甚至卖国的动机,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来考量。对于当时的国人来说,无论是破碎的山河,还是无能的政府,都难以让民众对“中国必胜”产生信心,中国能够胜利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历史上,中华民族曾数次被异族入侵奴役,也发生过屠城。然而,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提前投诚带路的汉奸很可能成为开国功臣。因此,一部分人选择血战到底、杀身成仁,一部分人选择成为“识时务者”和入侵者分享胜利的果实,是有一定的现实土壤的。如果日本最终胜利了,他们就不是“汉奸”,而是既得利益者。
这种对汉奸群体的复杂书写,恰恰彰显了民族自信与文化反思的勇气。当我们的文化自信足够强大时,便能够超越简单的道德审判,拥有足够的自信去正视这样的一个群体的存在,并给予他们一定的理解和审视。过去那种对汉奸标签式的谴责,某种程度上是民族创伤的心理防御机制。而今我们敢于正视这类群体的挣扎与选择,标志着国人的民族心理已经从受害者心态向主体性认知转变。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的以史为鉴,从历史的泥潭和伤害中走出来,历史的教训才能真正转化为面向未来的智慧。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南京照相馆》以“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为创作主旨,通过平民视角叙事和克制的影像表达,以坚定的历史自信为时代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
撰稿| 高晓庆 省影协驻会干部